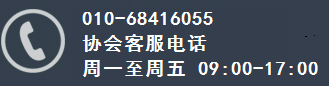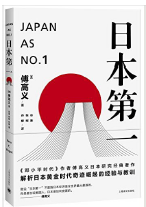
書 名:《日本第一》
作 者:(美)傅高義
出版社:上海譯文出版社
原作名:Japan As Number One: Lessons for America
譯 者:谷英 / 張柯 / 丹柳
這是一本37年前寫就,今年在中國出版并經(jīng)原作者重新作序的“老書”。
書名為《日本第一》,作者是著名的東亞研究專家傅高義——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前主任。在上個世紀(jì)60年代,傅高義在日本居住了兩年,這短短的旅居生涯竟然讓之前對日本“一無所知”的傅高義,對日本產(chǎn)生了強烈的興趣。“日本這個國家使我大感興趣,超出我要搞的社會學(xué)概論范圍”,傅高義后來回想起那段經(jīng)歷時如此說道。正是憑借著這種好奇心,后來傅高義不僅對日本的中產(chǎn)階級進(jìn)行了專題研究,更是在1979年出版了一部全面描寫日本社會的著作《日本第一》。
現(xiàn)在的傅高義名滿天下,還著有《鄧小平時代》一書。《日本第一》曾在美國風(fēng)靡一時,美國人確實從日本受教,至少學(xué)到了如何改善質(zhì)量控制。“我感到本書曾對美國產(chǎn)生相當(dāng)影響,因為更多的美國企業(yè)因此研究了日本公司取得高質(zhì)量的途徑。此書在美國也促進(jìn)了大家關(guān)于美國孩子為什么在國際成績測試中不能取得更高分?jǐn)?shù)的討論。當(dāng)日本公司在美國建立了制造廠的時候,許多美國經(jīng)理與工人既因日本質(zhì)量控制與效率的成功而感到印象深刻,他們也學(xué)到了日本人所發(fā)展的工廠管理方式。”
傅高義對日本成就的總結(jié)是在上個世紀(jì)70年代末所做出的。30多年后的今天,世界格局儼然已經(jīng)發(fā)生了巨大的變化。這本三十多年前的著作現(xiàn)在中國出版又有何意義?進(jìn)入21世紀(jì)后,日本經(jīng)濟(jì)發(fā)展速度的放緩,中國在經(jīng)濟(jì)領(lǐng)域取得全球矚目的成就,曾經(jīng)充滿的那股向日本學(xué)習(xí)的風(fēng)氣,開始出現(xiàn)了某種微妙的變化。有人認(rèn)為,日本人表面禮貌卻難以掩蓋對中國的敵視,因此應(yīng)對其予以警惕;有人則認(rèn)為,日本早已陷于政治和經(jīng)濟(jì)問題中無法自拔,已沒有資格再作為中國人的榜樣。相比之下,那些認(rèn)為應(yīng)當(dāng)繼續(xù)向日本學(xué)習(xí)的中國人則少之又少。那么,對于今天的中國來說,是否有必要將一個經(jīng)濟(jì)指標(biāo)上遲滯的國家作為轉(zhuǎn)型期可供借鑒的榜樣?
在新序中,傅高義專門解釋了這一點: “本書中我所描述的日本諸多強項,不僅對發(fā)展中國家,而且對于像美國和中國這樣的大型經(jīng)濟(jì)體,迄今仍能給它們提供啟迪。目前,日本仍在一些領(lǐng)域表現(xiàn)出色,值得學(xué)習(xí)。日本人民收入相對均衡,只有較少的極端富裕或貧窮。日本非常富裕的人群不多,絕大多數(shù)家庭有著中產(chǎn)階級的收入。日本腐敗程度低,產(chǎn)品質(zhì)量高端。日本醫(yī)療保健十分普及, 而且價格合理。日本犯罪率極低,民眾客氣有禮。日本污染水平較低,城市干凈。日本人民具有誠信,接受維護(hù)社會秩序的責(zé)任。同本書三十五年前首次出版時比較,今日日本的情況已大不相同。但本書那時所講述的日本做得很好的那些精華今天依舊還在,本書所講述的日本之成功仍然提供了值得大家學(xué)習(xí)的榜樣。”
傅高義認(rèn)為,日本的成功起碼體現(xiàn)在七個方面。這七個方面包括:知識、政府、政治、大企業(yè)、基礎(chǔ)教育、福利和犯罪控制。這七個方面可以歸入三類制度方面,比如知識和基礎(chǔ)教育體現(xiàn)出日本在教育、情報制度上的成功;而政府、政治和大企業(yè)的成就,則可以歸類為組織制度上的成功;至于福利和犯罪控制,我們則可以將其看作是社會管理制度上的成功。
日本大企業(yè)的規(guī)模與我國大型國企相仿,也時常有政府退職人員進(jìn)入大企業(yè)做高管,日本企業(yè)講究年資看重輩分,他們是如何避免官商勾結(jié)?如何晉升突出人才?如何避免庸才當(dāng)?shù)溃吭跈C(jī)構(gòu)組織方面,日本企業(yè)和行政機(jī)構(gòu)看上去層級森嚴(yán)而且流動性很低,供職于其中的職員和公務(wù)員大部分都是“終身制”。于是,很多人認(rèn)為,這樣的機(jī)構(gòu)制度會令組織陷入僵化,最后導(dǎo)致人浮于事。但傅高義卻認(rèn)為,在這種組織制度下,職員或公務(wù)員才會為了避免被制度邊緣化,而更努力地奉獻(xiàn)自己的能力和精力,幫助機(jī)構(gòu)實現(xiàn)發(fā)展目標(biāo)。另外,在這樣的組織制度下,職員也會對組織更加忠誠,職員之間也更加團(tuán)結(jié),這有助于長期規(guī)劃和大型項目的實施。相反,歐美過于強調(diào)個人的組織制度,使得員工與企業(yè)或機(jī)構(gòu)的利益很難保持一致,這也就不利于商品質(zhì)量維持在高水平,長遠(yuǎn)來看,也不利于企業(yè)長期目標(biāo)的實現(xiàn)。作為一個亞洲國家,日本卻難能可貴地在社會管理上同樣實現(xiàn)了現(xiàn)代化。正如很多人所觀察到的,日本無論在環(huán)境管理、社會治安還是城市規(guī)劃上,都顯示出強大的組織能力。盡管,日本也曾經(jīng)歷過環(huán)境污染的問題,也同樣遭受著犯罪案件的困擾。但我們不得不承認(rèn),今天的日本的確比大部分國家都要顯得更干凈、安全和井然有序。
就在《日本第一》出版不到10年的時間, 日本經(jīng)濟(jì)即遽然陷入了衰退。直到今天,日本仍然未能走出衰退的陰影。在整個世界格局中,日本處于衰落之中。而這正顯示出,日本的發(fā)展模式本身也有許多值得反思的地方, 但是日本的現(xiàn)代化進(jìn)程確實是有目共睹,即使在經(jīng)過“失落的二十年”后依然是個現(xiàn)代化的國家,這位鄰居的得與失也許對一水相隔的我們最有啟示意義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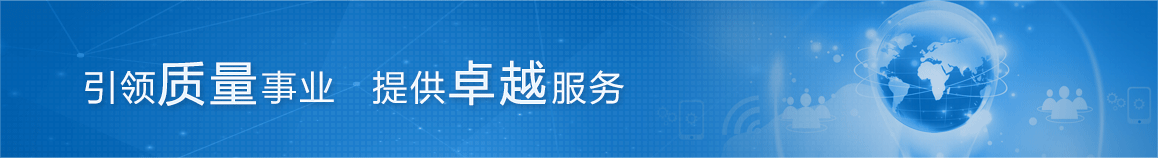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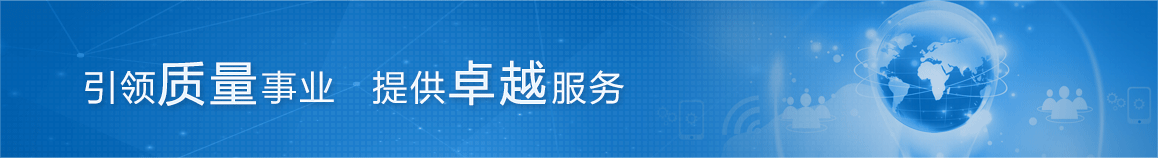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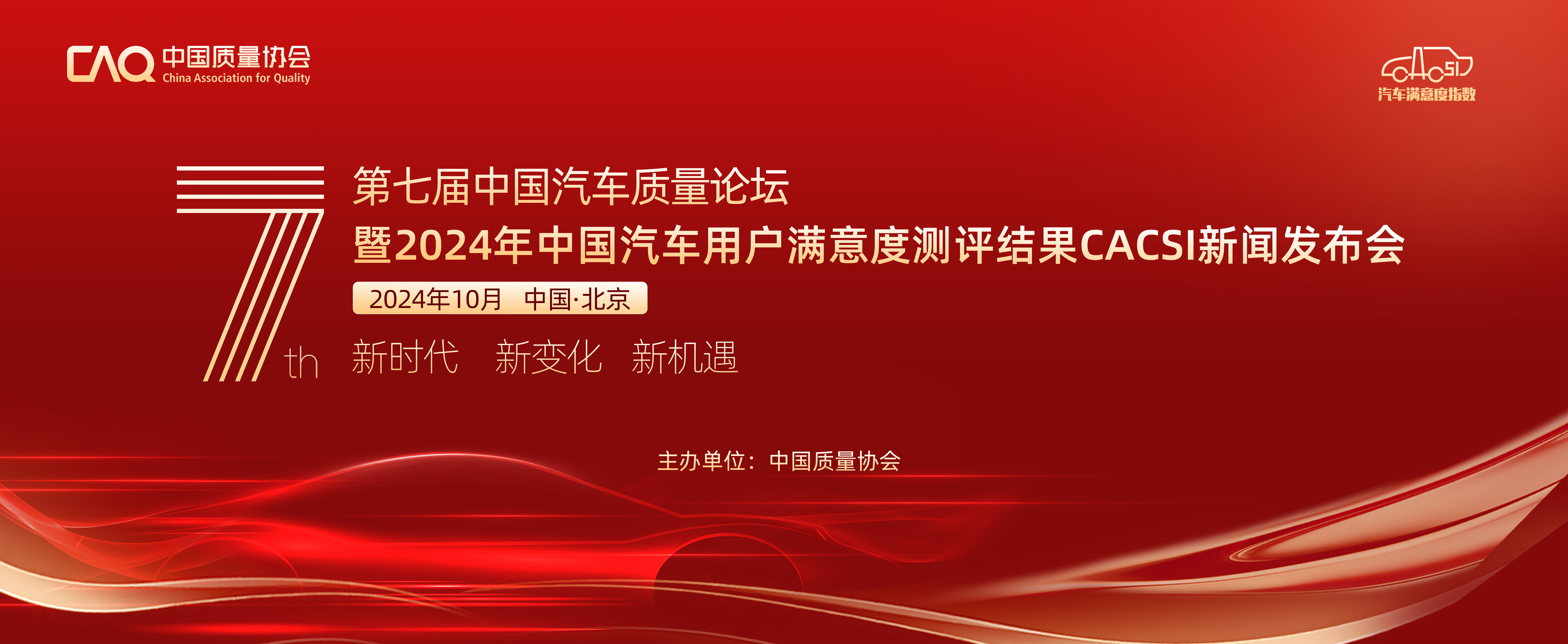 2024年第七屆中國汽車質(zhì)量論壇暨20...
2024年第七屆中國汽車質(zhì)量論壇暨20...